《美國50家最佳唱片店》是一系列文章,我們試圖在每個州找到最好的唱片店。這些不一定是價格最優惠或選擇最豐富的唱片店;你可以使用Yelp查找。每家特色唱片店都有一個超越貨架上商品的故事;這些商店有歷史,培養社區意識,並對經常光顧它們的人們有意義。
那是個雨天,當我造訪梅洛迪至尚,一家位於夏洛茨維爾市中心的行人購物中心第四與水街角的唱片行。乍看之下,第四街交叉口是條普通的房地產街區,沿著滿是舒適小店,比如樂士和自然浮現的精品店,這些店都圍繞著梅洛迪至尚。只有當我靠近時——當我看到磚牆上的粉筆塗鴉,堆在路上的濕花——才知道這裡發生了一些不同尋常的事情。
距8月12日的事件已經過去將近三個月了,當時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在一次襲擊中駕車衝入反抗示威者的人群,導致32歲的律師助理希瑟·海耶喪生,19人受傷。那次暴力事件幾乎發生在梅洛迪至尚的門口。然而,儘管8月12日的故事與夏洛茨維爾那幾乎被掩埋的仇恨和偏見的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梅洛迪至尚的奇蹟在於它顯示相反的恆久性——它既是城市音樂社區的深深嵌入的錨點,又是一個從外部世界逃生的避難所。
去年作為學生剛到夏洛茨維爾時,我確實感到有點陌生。這種感覺並不是特別新奇——我的高中班上有很多人都進入了弗吉尼亞大學,這是一所秋天拍照極佳並且以新古典建築和迷人傳統擁有可觸摸感歷史的名校(學生們親切地稱創始人托馬斯·傑佛遜為“T.J.” 或“傑佛遜先生”)。如果你來自我成長的華盛頓特區郊區,那種單調卻高檔的地方,並且願意忘記校園的核心地區(在弗吉尼亞大學的語言中稱為“校園”)是由奴隸勞動所建造的,那感覺尤其理想。
我也投入了這種神話,即使我知道這是人為製造的;像大多數從郊區來的無意識的亞裔少女,我感到一股不必證明我理應在這樣一個充滿故事的地方佔有一席之地的強烈需求。我不夠熱情去成為一個姐妹會女孩,因此我半心半意地申請了學生電台,當我被接受時感覺有點假。我特別擅長在房間演出時,在廚房或冰冷的前台階上漫不經心地聊天,那些人比我更美麗更自信,同時給人一種我屬於這裡的印象。儘管我一直以為自己已經克服了那種令人尷尬的青少年時期對融入的需求,但來到大學後,我驚恐地意識到,我肯定仍想要很酷——或者至少讓我喜歡的人覺得我很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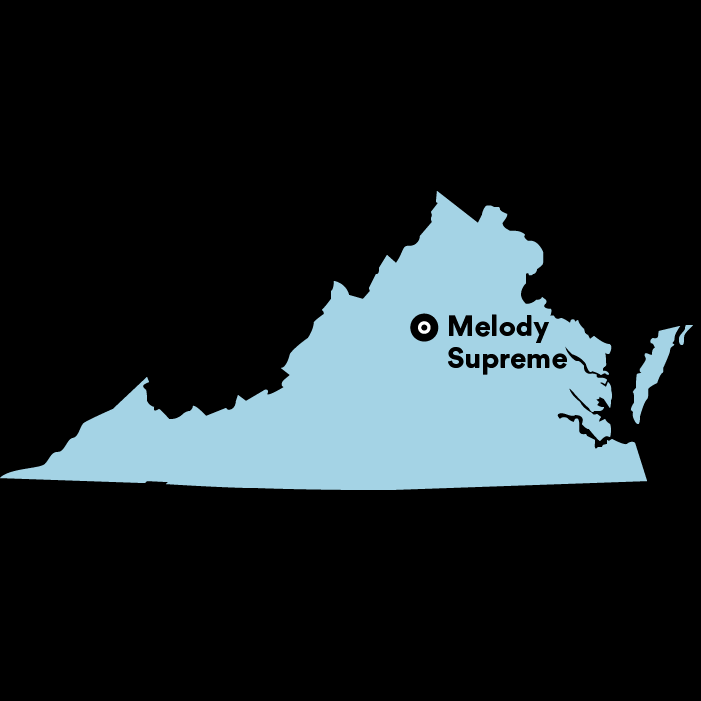
實際上,我的音樂品味是相當不成熟的——我擁有的第一張專輯是高中音樂劇原聲帶,我真心喜歡“We Built This City”以及所有80年代合成器風格的單曲,就連我媽都覺得這些歌曲俗氣,我在和高中戲劇班一起在百老匯看漢密爾頓時多次哭泣。那時和我並不是男朋友的男孩(但我還是非常希望他能喜歡我)是一名音樂人,他偶爾會發他的作品樣本給我,並請我給予反饋,而我總是用一些模棱兩可、偽詩意的詞語來掩飾自己不存在的技術知識,比如“閃閃發光且引人入勝”或“像早期的Modest Mouse被安置在感官剝奪箱中”。但我喜歡這種奇怪、理智的發現感,雖然我不完全確定為何我喜歡它——我發現菲利普·格拉斯是誰時,他答案出現在一個鬥智問答比賽中,我了解到自己無意識的喜歡12世紀修女希爾德加德的作品,是因為她的名字出現在一堂關於中世紀基督教女性的課程中。
此外,我室友才是真正的黑膠收藏家,不是我。每當談話轉向高級音響設備或限量壓片時,我都感覺像個冒牌貨,但我仍然感激能和他一起同行。我們第一次一起去唱片行時,我完全不知道在找什麼。
事實證明,梅洛迪至尚對我來說既陌生又像家一樣。這家商店已經快八年了,相對年輕,且有著非常規的起源故事。它於2010年由法國出生的攝影師Gwenael Berthy創立,他在40歲左右決定轉向獨立唱片行生意。他直接從法國來到這裡,短暫住在里士滿,然後獲得了夏洛茨維爾市中心的這片空地成為梅洛迪至尚的現址——據報導,這是一個用了九個月準備的過程。搬遷時,他在夏洛茨維爾完全不認識任何人。
梅洛迪至尚的成功見證了Berthy對細節的嚴格要求,這在商店的精心策劃的唱片選擇中顯而易見。當我終於逃離持續的毛毛雨,踏進商店抬起頭來時,我有種強烈的衝動想要探索,即便我知道我可以在這裡花上好幾個小時,卻未必能挖掘一半的奧秘。
儘管明亮、乾淨的零售空間夠小,能完全放入我的視野範圍內,但瀏覽其深厚的黑膠收藏帶來一種在秘密博物館觀光的欣喜之情。我在古典音樂部分看到的第一個名字很陌生——在必須的巴赫和貝多芬之前,我發現了文藝復興時代的作曲家和長號手Bartolomeo Tromboncino的Frottole,稍後我了解到他臭名昭著地謀殺了妻子,並受雇於盧克蕾齊亞·波吉亞。鄰近的箱子,標籤“20世紀前衛電子莫格”,包含一張1978年的唱片,名為電腦世代。它有個明亮的抽象橙藍封面,曲目比如 “In Memoriam Patris” 和 “Synapse for Viola and Computer”,即便在這樣顯然過時的物品中,也勾起了外星奇觀的想象。在能夠擁抱我無知的過程中,一種奇妙的自由感油然而生。我喜歡在這裡完全當個觀光客,而不需表現出任何表面的獨立音樂品味。推薦展示強烈推薦一張日本kraitrock樂隊Minami Deutsch的同名LP,我在手上寫下名字,打算之後搜查。
在另一個裝滿七英寸單曲的紙箱中,我挖掘出一張The 5th Dimension的 “Living Together, Growing Together”——一首由Burt Bacharach和Hal David為1973年臭名昭著的電影失落的地平線創作的曲子。它包在一個印有糖果色、彩虹從花和雲中湧出的封套中,旁邊是一個顯眼的RCA標誌。在電影原聲帶的箱子中,我找到一張仍然包著塑封的壞頻道,這是1992年的一部搞笑科幻片,也遭到評論家批評,但恰巧擁有藍牡蠣樂團的原創音樂。
在它後面,我無意間發現了Phenomena的原聲帶,那是我最喜歡的電影之一——這是一部1985年由Dario Argento執導的恐怖片,主角是前迷宮的Jennifer Connelly,她在瑞士扮演一個有心靈感應的女學生,充滿血腥謀殺和令人噁心的蟲子畫面。Goblin的配樂充滿了我一直喜愛的那種80年代殺手片合成器聲音,Berthy似乎注意到我已經深情地撫摸這張專輯一段時間了。他提到這是一個難得的發現,我急切地問他是否有其他Argento電影的原聲帶,比如更知名的陰風陣陣或血紅,但他說沒有。但是這個發現的刺激感讓我感到無比的自信。
我知道沒有客觀理由說服自己購買這些唱片,但它們似乎有著某種神秘、誘人的力量。它們的迷人之處不僅僅在於其奇特或好奇心,而在於其自身作為文物的意義——我忍不住思考每張唱片的擁有者的血統,他們經歷的漫遊,以及它們如何最終來到夏洛茨維爾。被當地博客問及黑膠與其他音樂格式有何不同時,Berthy曾回答,黑膠的實物感和感官性是其他媒介無法比擬的:華麗的封面藝術,內頁注釋和背頁文案,以及我們小心翼翼地放在唱機上的這張閃亮的圓形黑色唱片。儘管我自己甚至沒有黑膠唱盤,但這種實物儀式的冒險感仍然深深吸引著我。
此外,梅洛迪至尚的豐富收藏也不忽視當地樂隊。夏洛茨維爾的音樂場景並不大,但我還是認不出一些名字。New Boss是一個活躍在當地演出的心理搖滾樂隊,但我不認識Red Rattles或Invisible Hand,前者是車庫靈魂二人組,後者是光滑的力量流行四重奏,曾被吹捧為那年梅洛迪至尚開業六年前被譽為“夏洛茨維爾最受歡迎的獨立搖滾樂隊”。我試圖通過臨時谷歌搜索挖掘更多信息,但這兩支樂隊似乎目前處於低調甚至完全解散的狀態。他們的消失讓人感到有些傷感,再次我不得不克制住自己想把唱片箱中的每一張唱片都抓起來,以免忘記他們的故事的衝動。
當我最終離開商店時,雨依然在下,但這次濕冷刺骨的寒意卻變得清晰,而不是麻木。我開始注意世界上的最小細節。當我穿過街道走近臨時紀念碑時,我看到一個嶄新的紅色Solo杯,裡面裝滿亮橘色的康乃馨和金色的玫瑰,在更老、更褐色的花朵中。愛與抵抗的呼籲以及無數的紀念希瑟的承諾之間,有一條粉筆畫成的淡藍色鈴鐺鏈。沒有人忘記這裡發生了什麼,但在嚴肅的紀念之中,仍有這些小小的、意想不到的奇跡。
接下來,我們將前往紐約的唱片行。
Aline Dolinh是一位來自華盛頓特區郊區的作家,對80年代的合成器流行音樂和恐怖電影原聲帶充滿熱情。她目前是維吉尼亞大學的本科生,並在推特上以@alinedolinh的身份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