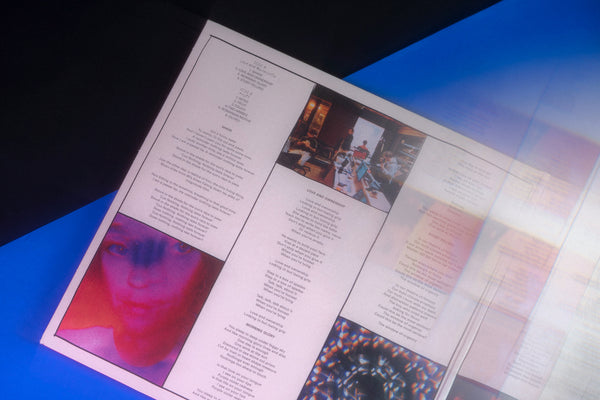VMP Rising 是我們與新興藝術家合作的系列項目,將他們的音樂壓制成黑膠唱片,並突顯我們認為將成為下一個大熱門的藝術家。今天,我們將介紹 Shadow On The Wall,這是 TATYANA 的首張 EP 專輯。
n照片由 Nwaka Okparaeke 提供
隨著來自倫敦的FaceTime鈴聲響起,TATYANA從打盹的狀態中確認,這裡的下午和她的晚上的時差有六個小時。我迅速詢問關於我這邊的情緒和她在英國的生活之間的區別;無論是什麼口號,這些全有全無的含義都未能影響一大群人,他們為自己而行,毫不在意。TATYANA和她的母親住在一起,採取每一項預防措施來確保她的安全,同時對於這種不確定性保持著適應能力。無論多麼快撥號,大家都很容易聯繫,但無論如何也容易錯過。
像許多身處千禧世代和Z世代交界的人,TATYANA的轉瞬即逝的生活故事對於許多二十幾歲的網絡世代來說似乎已成為新的常態。雖然屏幕幾乎可以把人在任何地方,但TATYANA已經去過幾乎所有地方:她是英國父親和俄羅斯母親的孩子,兩人離開蘇聯尋找新生活,TATYANA的童年是以“無根”方式度過的,隨著她的家庭尋求工作和穩定而變換家園和國籍。她擁有英國護照的驕傲和特權,但在她的年輕歲月裡,從荷蘭到新加坡以及其他地方,建立並帶走了許多不同版本的自己。自2017年重返倫敦以來,她再次有機會在深愛的城市裡建立自己。
“當你回到一個你之前待過的地方,並且你帶著所有新的身份和經歷,這些與你當下所在的地方無關時,你會感覺到自己碰到了過去的鬼魂,”TATYANA說。“你會想,‘哦,我記得在這裡,但我現在的感覺完全不同,我感覺自己是個不同的人,人們也會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我。’我不覺得我屬於任何地方;就像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說是我的家。就是這樣。我覺得這將是一種終身的旅程,努力尋找一個我覺得屬於我的世界。”
無論是通過翻唱和豎琴視頻獲得病毒式傳播,還是在伯克利音樂學院和BRIT音樂學校的演出,TATYANA的23年充滿了學術與社交的交集。她回憶起自己年輕時的大魚症候群,當時是新加坡高中的唯一幾名音樂家之一;當你是學校的藝術家時,想必達到超級明星的道路是勢在必行的!但搬到波士頓進入伯克利後,她被迫面對周圍藝術家的激烈競爭,經歷了多次自我意識的死亡,並對學習過程謙卑。這段經歷將她融入美國黑人爵士音樂的傳統,同時使她擺脫創作的孤獨性,促進了她在社區背景中的快速發展。然而,這種象牙塔的交換——票價的代價——給她的才能上了限,這在她進入之前是沒有的。
“當你經歷這樣的機構時,你[無法]失去最初讓你想創作音樂的那部分東西,”TATYANA回想道。“因為你的腦海中充滿了關於你應該做什麼以及事情應該聽起來怎麼樣的大量信息。這可能會引導你走向一些也許你不應該去的地方。因此我不得不關掉我腦中的那部分。畢業後我一年左右無法聆聽音樂,因為這很困難;我無法關閉那種分析和批評的腦部運作,當你在這些地方發展出來時。”
2017年搬回倫敦後,TATYANA將一場萬聖節盛會視為她找到社區並在支持環境中繁榮的轉捩點。她渴望了解城市的運作,並被音樂的節拍所吸引;她當時不是電音歌手,但這激發了她將舞曲融入她正在塑造的新自我的渴望。她找到了自己的同伴,並在同樣的倉庫、觀眾和異教節日中——兩年後,她在俱樂部表演自己的作品,獲得了壓倒性的好評。
藝術學校之後的生活使TATYANA在公共場合逐漸聚集自己,慢慢準備進入聚光燈,同時找到真正製作音樂的方式。作為@blueharpgirl,她通過將才華濃縮成Instagram的方框,積累了超過2萬名關注者,進行翻唱和聲音片段,並加入合宜的可點擊“合成美學”。但她的內心是一位流行歌手,開始下一章,發行她的Shadow On The Wall EP。至今只有兩首單曲,這一轉變結合了所有的TATYANA,同時在她的螢幕外生活中提出許多相似的問題:她想成為誰?她希望從哪裡來?當不再是穿著短上衣並演唱翻唱歌曲的@blueharpgirl時,她的支持者中誰會跟隨她?
“對我來說,一個一直是非常私人的夢想(和某種現實),現在我將其公之於眾,”TATYANA說。“我會犯錯,從第一天起不會完美,但我知道在我所創造的這個藝術人設中,還有太多的事情要說和做。我覺得這會很有趣,我努力以積極的態度看待它,因為我認為會有一些音樂能夠與人連結。所以無論是新粉絲還是老粉絲,他們都可以來看我,希望能成為一隻從毛毛蟲變成蝴蝶的過程。我和大家一樣在學習,因此我覺得一切都會好的。”
TATYANA的首張作品將她所有的強項融為一體,形成一種夢幻的流行音樂,深具浪漫情懷並沉醉於模糊之中。她首先承認自己“活在白日夢中”,這五首歌曲的努力讓她在追求好事的同時,閃避定義和穩定。它直接反映了她自身的短暫,每一張專輯都是揮霍並珍惜美好時刻的另一個嘗試,隨之而來的是對它們短暫性的投降;這更引起對感受、季節和人們的共鳴。她聲音的柔和能夠讓聽眾直接陷入困惑,這種欣喜的感覺很容易與她視覺美學的亮點相伴隨。這種吸引力在吸引中等待著,每一束花和長裙都是TATYANA音樂如何喚起感官的另一步伎倆,像思維時常困擾她一樣。
“在很多方面,我覺得那些歌曲在講述的是人而非實際的人,”TATYANA說。“因為我實際上是在和自己對話。所以它採取了一種夢幻的狀態,因為那些人甚至不是真實的,他們只是我編造的幻想,代表了我心中愛的人。我是在對他們說話——而不是對實際的人——因為我一直擁有非常生動的想像力。特別是作為孩子時,我的夢想和所思考的事情對我來說感覺如此真實。我創作音樂的部分正是那個內心的小孩:我所有的夢想都是現實,我和這些鬼魂,或投影所進行的對話,感覺它們會在某種程度上實現。即使最後沒有實現,但它們在音樂中依然真實。”
TATYANA對她的夢想的看法也反映了她對手藝的參與方式。作為一位創新的豎琴演奏者的學生——像Alice Coltrane和Dorothy Ashby這樣的名字出現在我們的對話中——以及古典俄羅斯作曲家,TATYANA醉心於超越她的古典訓練,並擴張她的樂器效果,同時專注於良好流行音樂的力量。通過在風格和傳統之間的灰色地帶運作,她朝向不尋常和原創的方向邁進,即使她步履在流行音樂的主題中。這是一個她無法具體描述的過程,然而,純粹的力量仍然是她不斷創作的重要原因。在最好的時候,她通過把自己沉浸在資訊當中來學習和重新學習,直到她脫穎而出時夠新鮮。
“我想在我個人的生活中,我也處於知道一切與感覺像個白癡之間的過程,意識到我需要自我教育或學習一些東西,”TATYANA說。“而對於音樂……我真的不想知道。寫一首歌的過程對我來說仍然非常神秘。每次它發生時,都感覺像是一場意外,或者就像我進入了某種恍惚狀態,出來時帶著一首歌,然後我會問,‘這是怎麼發生的?’這仍然非常神秘。我覺得如果我真的找到了我所做的事情的方式,那可能會毀掉它。我認為最好把它保持神秘,所以我努力讓它保持神秘。我試圖用儀式和一些可以讓我進入那種狀態的東西來掩蓋它,但我不想理解它。”
但TATYANA確實理解音樂的治癒力量,並努力將那股能量引導至她的實踐的科學層面和樂器的物理層面。她回憶起為安慰她的祖母的癡呆症而演奏音樂,感謝豎琴弦的震動作為一種她無法理解但卻可以視覺化的力量。仿佛TATYANA逐漸體現了她的選擇樂器:一個運用不確定性的容器,通過對誤解的信任來傳遞力量。她只能控制她的瞬間,儘管時間和空間始終在她周圍變化;現在她再次有機會在她自己設定的條件下進行振動,帶著真正連接的相同意圖。
“我認為流行音樂是治癒的,”她直言道。“我認為它是一種逃避,是普遍的。我只是喜歡愉悅、普遍的主題,並盡可能多地與人建立聯繫。我認為這其中有著強大的力量。但我認為風格真的可以是任何東西,而我開始理清自己從小就有的目標:‘我如何將這種神奇的樂器引入這一流派?像,我怎樣製作harp pop?’首先,你必須知道如何創作流行音樂,還必須會演奏豎琴,但我認為未來它將會融合在一起,我希望它在治癒特性上會非常強大。”